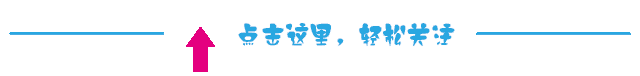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特殊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规约,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创作动机和宗旨便是为了完成救亡任务和革命历史的塑造。爱国激情掌控下的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并不特别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
诚然,在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如此的创作倾向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问题是,抗战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陈陈相因,同期或此后不乏邯郸学步之作。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与幽微复杂的人性被预设的判定简化处理。以至于有的论者认为抗战文学的抗战性消弭了文学性,救亡性压倒了启蒙性,抗战文学不过是宣传的代名词。尤其在少数民族抗战诗歌和戏剧方面,部分作家直接引入了大段的议论以及当下的政策宣传。“诗朗诵”运动和街头戏剧试验将此类创作推向极致,而诗歌和戏剧文学的蕴藉美则被无情地解构。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作品极大地强化了经世致用和政治教化的功用,遮蔽了人类自我生存和精神存在的在场。而文学一旦放弃了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索,一旦简化了对存在之思的追问,中国的抗战文学便很难与《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静静的顿河》等世界经典战争文学名著相比肩,更难以获得开阔而深邃的人类性品格。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图源于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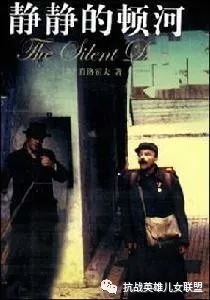
《静静的顿河》(图源于网络)
战争年代,郁达夫曾在《战时的小说》中判定:“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是不会出现‘伟大的小说’的。”原因是读者每日面对生死的考验,没有细读文学的闲暇,也不会轻易地被感动。然而时至今日,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70周年,我们的抗战文学依然不得不面对经典寥寥的遗憾与尴尬。事实是,只有切近人本的细部才能廓清历史,也只有书写广大民众在战争中的生存世态、精神样貌才能有效地切入战争的内核。当下我们的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书写仍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停留在简单的国家主义和暴力美学的展示中。更有甚者,将抗战题材的书写强行拖入消遣化、戏谑化和娱乐化的媚俗队列中,轻巧地放弃了严肃文学对人类存在境遇的勘探,对历史真实的质询以及对民族精神的重塑等重任。
令人欣慰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开始有意识地摆脱意识形态化和正史化的规约,转而以个人化、民间化的立场和话语重新叙述抗战历史。意图揭示出在诡谲的历史中个人、国族、乡土与抗日战争之间偶然的遇合。比如蒙古族作家乌兰的小说《富贵荣华的岁月》讲述了蒙古营子里的众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展示出的人性悖谬。与此相似的还有回族女作家白山的小说《冷月》,作家试图揭示出英雄史观所掩盖的生活真实及个体生命的无意义消殒。这些抗战文学的书写,消解了战争年代实用理性的紧箍咒,逐渐构建出新的审美视阈。
今天,当我们用回溯的视角来检视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书写时,还可以轻易地指认出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存在的其他缺憾——民族性质素不够充分;叙事艺术粗放;人道主义欠缺;存在之思的浅表折射以及对终极价值追求的匮乏等等。但即便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存在如上局限,也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它的历史功绩与作家们所作出的丰饶坚韧的努力。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不仅参与作家人数众多,而且众体兼备,他们用宏富的创作在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李辉英的《万宝山》和《最后一课》;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蒙古之夜》《沙漠中的火花》;马加的《复仇之路》《潜伏的火焰》《寒夜火种》;老舍的《火葬》及《四世同堂》等。小说之外,少数民族抗战文学中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散文也呈现出井喷式的创作态势。例如满族作家金剑啸、朝鲜族作家李旭、维吾尔族作家黎·穆塔里甫、蒙古族作家纳·赛音朝克图、纳西族作家李寒谷、彝族作家李乔、哈萨克族作家尼合迈德·蒙加尼等作家都为抗战文学的拓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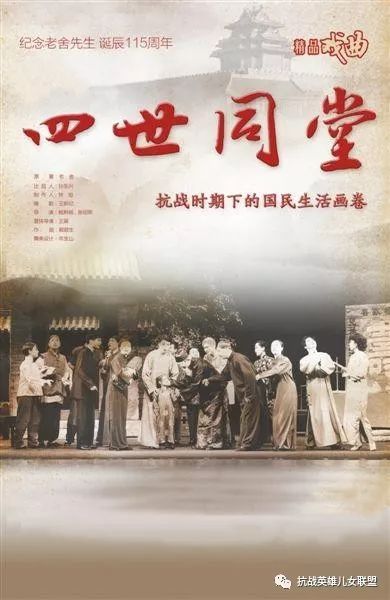
《四世同堂》(图源于网络)
少数民族抗战文学尽管存在着艺术上的“失”,但它在文学史上和救亡功用上的“得”也是不争的事实。它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空白,彰显了中华各族儿女对祖国的深切认同;携带着中国人民强大的自我更生能力及博大雄强的抗争力量。少数民族抗战文学馈赠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仅从这一维度而言,它理应获得我们的衷心珍爱和无尚敬畏。(文/乌兰其木格)
·END·
抗战英雄儿女联盟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