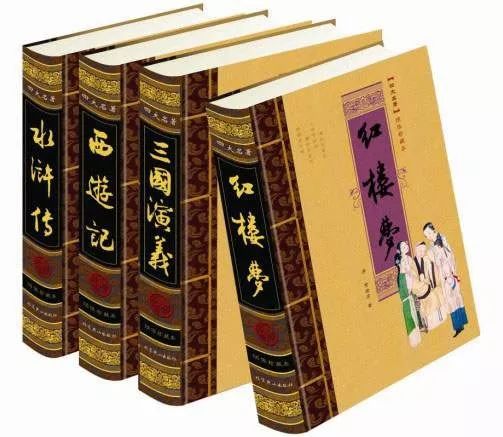
1
好多年前,慕名去附近乡村拜访一位年逾80的老者。据同去的校长事先介绍说,老者曾是国民政府时《开封日报》的编辑,古文学——时髦一点可换一个词语“国学”——修养深厚。当时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他留了下来。我们此去的目的是请他来校作一次报告。
老人中等个头,精神矍铄,腰板挺直,迎进送出决无半点迟钝缓慢,看不出农村辛苦劳动留下的痕迹。当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老人独居的小院地面湿润空阔;三间瓦屋两间厨房,是标准的农家院子;青砖甬道干干净净。
幽静舒适的院落,一进来似乎让人忘了周围的存在。
他说十多年来一直独居此处民宅。有一个儿子在不远处另一所宅院居住,但他不习惯和儿孙们住在一起。
言谈中,老人也对时下教师这个群体文学基础薄弱深有感触。他举例说曾到县城最好的小学去,问一名年轻老师“问渠哪得清如许”一诗中余下三句是什么,对方答不出来。我那时还年轻,忙背给他听。
老人同意来校做一次报告,但被他的儿子阻止了:父亲年岁太大了,不方便外出。
2
不久之后那位老者去世了。想起他时,我有时会想,如果我随便找一位身边同事来背背那首诗,他们会吗?其实现在我想明白了,他们可能不会,也似乎不必会。比如要是我教化学课,背会那首诗又有什么用处呢?是不是就如同我去问一位语文老师氦元素原子核外围电子数有几个一样?
读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古人煞费苦心地诉说着读书的意义所在,只是最后修齐治平的宏愿还是不如黄金屋、颜如玉的诱惑来得实在。但拿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范例来说教的同时,也似乎吓退了一部分人。以苦为美的自虐哲学在时下似乎行不通了。四大名著买来,堆在案头洋洋大观,但读得进去的人似乎也不多。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调查了3000名读者,得到一份“死活也读不下去”的书目排行榜,四大名著都在其中。文学固然是好东西,但看看曹雪芹蒲松龄等文学大师的贫寒生活苦涩人生,他们的作品也只能让人敬而远之。当代作家余华等人的作品当然值得读,但掩卷之余,想想他要说却又不敢说的犹豫,张着嘴巴嗫嚅“天凉好个秋”的样子,才知道莫言在高梁地里吼一嗓子的痛快。
3
《荷塘月色》是经典散文,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文章在选入课本时,编者曾删去了一部分文字。自从读了原文之后,编者就要面临着大众质疑的目光,这样做是对作者有意见还是对读者不信任?又有谁赋予你这样做的权力?
莫伯桑的小说《项链》是世界名篇,现在重读时,回想当时上高中时老师课堂上说是对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辛辣讽刺,觉得有点无厘头的味道了。个人命运固然无法自己作主,但那个遇到机会敢于大胆表现自己的美,遇到意外敢于承担责任的女子又有什么错呢?在丈夫面前耍个小聪明让他把私房钱乖乖交出来的女子,不是很可爱吗?如果把这点小聪明用在朋友身上简直是可怕可憎了。至于小资现在已成为流行的情调了。我们批评她难道是因为她漂亮吗?漂亮如果是错,那错也不在她。我们讨伐她,可能只是因为她让我们无地自容。
还有以前课本上鲁迅的作品总是被解读得过于政治化,吐一口痰也能解读出难以言说的意蕴,真是让人佩服无语。
教材的编者,还有考试的出题者总是处于不断为自己找理由的尴尬境地,不正是大家读书多了的原因吗?
其实不读书的一群人来教书才是最好,至少教材的编者要轻松多了。现在农村小学老师的门槛已降到专科,在提升待遇和降低从业标准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也可能是仅仅从经济上考量的结果,但是不是可以说是正在让不读书的人来教孩子们读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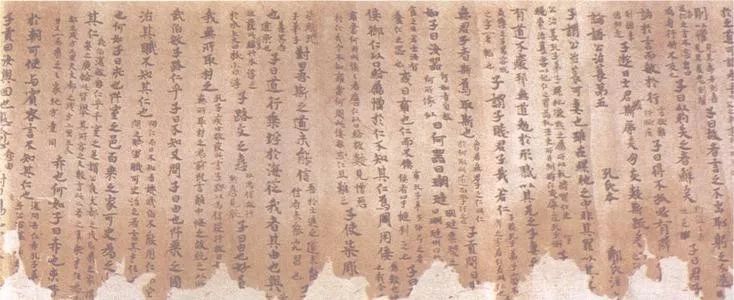
4
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一根甘蔗从稍部嚼起,当然会渐入佳境,可咀嚼之后还是吐去。一颗泡泡糖,如果要咀嚼到第一百遍才能得到最好的味道,一包茶叶如果要泡一百遍才能品到精华,那么百遍之后呢,也还是要唾弃。温故当然可以知新,但你所品味出的新,只是提高个人认知,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又能有多少新意呢。并且这里所谓的新大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是相近的学科,对社会伦理学或是人际关系学的反复品读,可能读不出自然科学的新知吧。把《论语》读到一千遍,也不可能读出地球是圆的吧。
三十年前我上小学时,我的语文老师对我说,世界上所有的书他除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外都读过了。我对他顿时肃然起敬。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代最不缺的是书,可最缺的也是书:他所知道的书除了马恩列斯等的著作之外,还有就是巴金的书了。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其实让人只读有限的几本书恰是不读书的另一种做法,甚至是最高明的做法。名著情结深入中国人心中,每人一个红本本,恰恰是读书的最大障碍。
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人于是说这本书太重要了。其实赵普的意思也只是说我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也识不了几个字,最流行的那本书也只读了一半。如果赵普的话可以证明一本书的重要性,那么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同样也治理好了国家又如何解释呢?
5
春秋末年晋国的韩赵魏三位异姓将军势力日益强大,最终踢开姬姓晋侯,将具有300年历史的晋国一分为三。最终周王室在公元前403年承认了这个事实,这一年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司马光痛惜于君臣等级体系的崩溃,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也从这一年开始写起。
分晋而成的三个国家之中,魏最繁荣。地处中央,土地富饶。魏国曾有人建议把都城迁到富饶的解州,这里有盐池,但有人说“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则公室贫”而没有成行。
让人民富裕是个好事,但是,“所谓自由的传统就是反抗的传统,而在一个经济明显改善的地方,自由的传统几乎是一定会被激活的”(《狂热分子》129页)。那些封建国家当然也说要让百姓富裕过上好生活,但骨子里是不是真心这样想呢?
其实读书也一样。明清时让儒者读好四书五经即可,但还是要变着花样出题考试,淘汰应试者。名著的每一句都出过题了,那么来个截搭题,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两个短句前后各选两个字“而立不惑”作为题目,你写写看吧。
即使这些书读好了,也未必真的需要明了其中的意思。科举考试到了明清时,答卷的样式比内容更重要。那些考官只以试卷形式来论成绩,因为这样做风险最小,形式可以有标准比对,内容则见仁见智的事。作为考官总是要面临太多监督或挑剔的目光,唯此也才能自保。
凡事都有两个原因,那个公开说出来的,很可能不是真实的。乾隆时要搞一个伟大的文化工程,整理古籍为《四库全书》。据史学家唐得刚说,那部书的内容比当时世界上大清朝之外的所有国印刷的图书之和还要多。但这个工作真实的目的是要成就十全皇帝的美名,同时要剔除古籍中对少数民族政权不恭敬的文字,结果是烧掉的甚至比整理之后留下来的书还要多。
如此苦心孤诣,大清朝还是完了。真是可惜……
谈读书
再谈读书
读书是个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