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北京的建筑,你第一反应,会想到什么呢?
是爬满老藤的胡同,耳边飞来老炮儿满嘴的京腔,穿过一处斑驳的砖雕拱门,看到落落的四合院。或是比四合院里大大小小的红砖厨房红得更深邃的朱砂红墙,墙内林立的金顶宫殿在日光下熠熠生辉。
只是,这座城的美,可不止于此。
顶着秋日早上7点半柔和的暖阳,跟着公交车一路摇晃到站,在手机导航的指引下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拐进一处安静的胡同,看着胡同尽头那扇巨大的中国风实榻大门,我不禁怀疑起导航的准确性:“明明找的是西什库教堂,怎么是这么中国风的地方?”,凑近拐角处的路牌,上面却写着跟导航上一样的位置——西什库大街33号……“那就,看看?”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近大门,转身,别有洞天。
中国风实榻大门内,是一条安静的石板路,如朝圣之路般,直通一座反射着金光的教堂——想必就是我要找的西什库教堂了。


早晨阳光的角度刚好,笼罩住整座教堂,映出圣洁的味道。

中国风的黄顶琉璃瓦碑亭和石狮子在教堂前坐镇着这哥特式的美丽,这座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教堂,见证了清帝国的兴盛、没落,陷入战乱的硝烟,终于等到了新中国的到来,回归了宁静。

走过石板路,看看教堂的不同角度。

四面八方笼罩着教堂的阳光穿过大小不一的玻璃花窗,把教堂内照得五彩缤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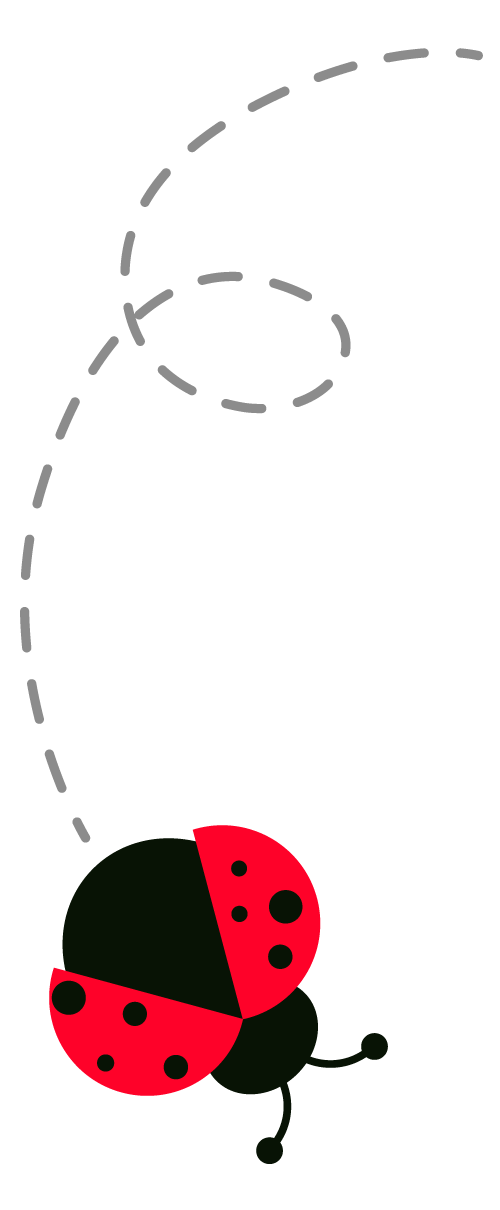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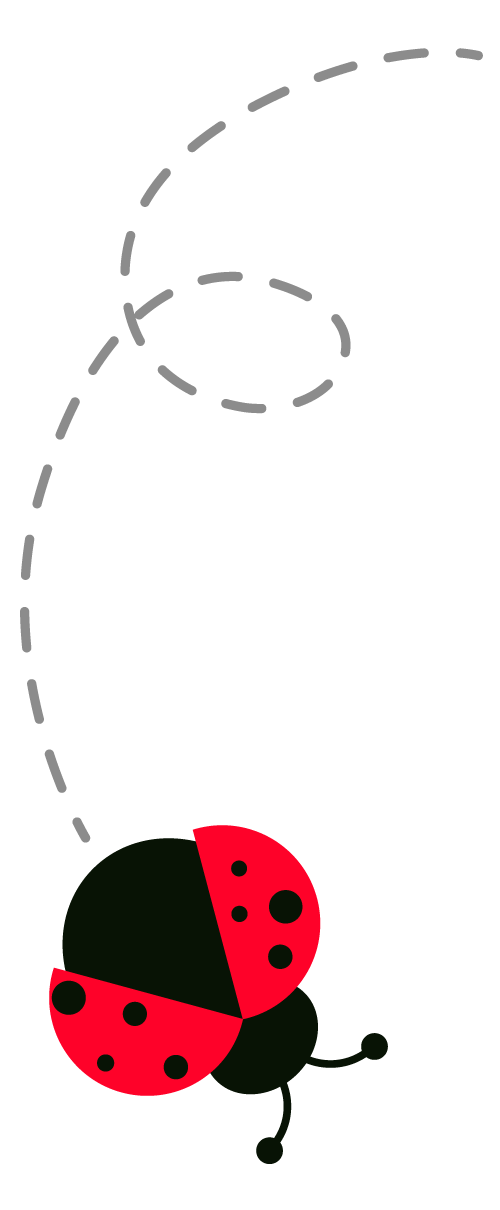
肚子开始叫唤,意识到还没吃早饭,跑到附近有名的西四包子铺吃了二两皮薄肉多的猪肉大葱,一口咬下,满嘴浓汤。

不舍得教堂的美丽,吃过早饭后又回到教堂,不再是过早的时候,通往教堂石板路上多了几位操着地道的北京话的大爷大妈,原本带着神圣味道的石板路瞬间被渲染上了烟火气,居然出奇的协调。
北京这座城,见证了太多,包容了太多,他的美,或许像阳光明媚的早晨操着地道北京话的大爷大妈带来的烟火气一样,和世界的另一端文化相碰,都如此和谐美丽。

西什库天主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两位天主教教士洪若、刘应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疾病,因而获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一代的一块地皮,得以建筑教堂,这所教堂便是今天西什库教堂的前身。
清朝中叶,民间反对天主教的势力与天主教会不断发生摩擦,清政府于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查封了蚕池口天主教堂,并没收了全部教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教会归还了教堂的土地,同治三年(公元1868年),主教孟振生主持在北堂原址建立了一座高大的哥特式建筑,由于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高大的教堂钟楼引起了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不悦,经过与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的交涉,教会同意将教堂迁往西什库,由清政府出资修建新的教堂建筑,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新式建筑正式落成。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6月15日傍晚,由端王载漪所率领的一队义和团开始进攻西什库教堂。6月17日起,清军也参加了进攻。但是教堂依旧顽强坚守。由于缺少粮食,经过半个月的围困后,教堂内的人员将作役用骡马和战马全部吃光,并且开始食用院内的树皮和野草。驻守部队的指挥官和副指挥官以及教堂的主教陆续战死。同年8月16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组建了专门的解救队,才将轰动一时的西什库教堂事件告终结。(义和团围攻、教徒坚守、联军解围三段为庚子事件)庚子议和后由清政府赔偿出资重修了损毁严重的西什库教堂建筑,形成了如今的西什库教堂的建筑群。
在1958年的“献堂献庙”运动中,西什库教堂被上缴国家,教堂收藏的教会藏书,各语种的“摇篮本”早期印刷图书和和一批稀见文献,被运出教堂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1985年中国拨款重修,修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1984年西什库教堂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文 | 郭凌宇 朱哲宇
本版编辑 | 通讯社记者 林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