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公众号” 可以订阅哦! 作者简介
任小燕(1978-),女,江苏宿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试论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多重来源
摘要
作为民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大学治理制度,大学董事会制度受到了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西方教会管理制度、近代公司管理制度、晚清传统书院董事制度等多重影响,存在着多重制度之源。该制度由于办学主体与管理理念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并在学校与政府的治校权力博弈中逐渐趋于统一。
关键词
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教会管理制度;近代公司管理制度;传统书院董事制度
一、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多重样态
随着清末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出现,大学董事会制度开始形成,随后在部分公立大学中也一度出现①。大学办学主体存在西方教会、民国政府、商业精英、社会力量等多重主体,因而大学董事会组织者也存在西方教会主导下的西方传教士、学习美制的留美学者、深受传统理念影响的儒家精英等多重身份,因文化或组织背景不同而呈现出迥乎不同的大学管理理念。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在董事会规模、实践功能、权力归属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
董事会规模上,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规模大小不一,尤其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作出严格的立案规定之前,这一特征十分显著。大学董事会规模,小则三人,或则十人左右,多则达百人。三人董事会、百人董事会均十分罕见。三人董事会见于私立厦门大学以及五四时期的清华学校,便于将治校权高度集中。百人董事会见于中国公学,该校董事人数众多,遍及全国各地,多是社会名流或一次性投资者,难以召集会议和正常运作。十人左右的董事会较为普遍,比如私立南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以及绝大多数教会大学。
实践功能上,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主要有筹集资金、社会沟通、安全庇护、校政决策等功能类型。筹集资金是董事会的基本功能,不论教会大学、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均不例外。私立南开大学等校与多个投资渠道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比如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保持长期合作,接受其定期经费资助。比如国立东南大学,其办学资金多半来自地方筹资,而非政府拨款。许多私立大学为了博取竞争资本、吸引生源,还聘请了达官显贵、文化名人为校董。比如大夏大学聘请了孙科、居正、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王正廷等政要为校董,复旦公学甚至由交通部次长于右任亲自组织董事会,聘请孙中山、王宠惠、陈其美等政要为校董。同时,私立大学往往通过拉拢地方势力,以维护学校运行的正常秩序与安全。比如,几乎所有的上海私立大学都聘请了杜月笙为校董。杜月笙不仅赞助学校教育,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社会势力,维护地方秩序和学校安全。此外,有些大学董事会如东南大学、清华学校的董事会,还一度取代评议会而具有校政决策功能。
权力归属上,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主要有教会控制、外行治理、政府干预、商人决策等制度形态。“教会控制型”董事会特指教会大学董事会,教会大学治理权由教会控制,董事由教会指派传教士担任,董事会是教会意志和决策的执行者。“外行治理型”董事会如私立南开大学董事会,主要由政府、学者、军阀、商人及社会各界名流等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大学治理,董事会负责提供学校决策参考,虽有政府官员参与其中,但仅作为官方代表列席,并不参与校内事务决策。“政府干预型”董事会,如交通大学、清华学校董事会,董事主要由大学所隶属的政府部门的官员担任。政府部门不仅是大学办学资金的主要出资者,同时也是校政决策者。交通大学、清华学校的董事分别来源于交通部、外交部,两校董事会亦分别成为交通部、外交部内部派别之争的角逐场。“商人决策型”董事会,如私立厦门大学董事会,董事主要由陈嘉庚家族公司的核心家族成员担任,陈嘉庚家族公司及核心成员不仅是学校投资者,也是校政决策者。
鉴于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巨大差异,学界普遍认为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是对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效仿这一说法就显得过于笼统,缺少有力的制度解释。一些留美学者如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等,的确是学习和借鉴了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然而,西方教会在华办理的教会大学,却由于教会组织的宗教特殊性、教派差异性而很难简单归于此类。众所周知,近代美国大学完成了从“宗教性”到“世俗化”的转变,美国大学董事会是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下的一种共同治理模式,而不再是殖民地时期的教会控制模式。此外,在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形成了传统书院董事制度及董事观念,并对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故而,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并非仅仅源于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一端,也并未仅仅受制于传统董事观念,而是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多重制度渊源。由于办学主体社会角色、组织结构、管理理念的不同而造成了制度选择与建构的差异。
二、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之本土效仿
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经历了殖民地时期的教会办学阶段以及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世俗办学阶段,最终形成了以多元资助、大学自治为特征的“外行治理”董事会模式。随着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的转型,美国大学与美国社会发生着广泛的联系,董事会成员职业遍布了企业主、资本家、银行家、律师、教育家、牧师、医生等职业,并且占据了董事会成员总数的八成之多。董事选举方式以共同选举、校友选举为主。大学的发展定位与方向由董事会和校长控制。在职权定位上,董事会为学校筹集捐赠,指明发展方向,审批院校预算,负责聘任校长[1](P100)。同时,多数大学校长“越来越成为实用主义者、学术帝国的建造者、资金筹集者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他们更看重那些给大学带来声望和经济收益的政治活动”[2](P138)。
20世纪初,多数由国人办理的私立、公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或模仿了同期的美国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董事会制度。从南开大学创办者严修、张伯苓对于美国私立哥伦比亚大学考察与学习行政管理制度的情况,东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教务长陶行知等人都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并研究教育的情况,从民国教育部主要官员赴美考察和制定政策的情况来看,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美国大学董事会模式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管理思想,对民国时期私立、公立大学董事会制度发生了重要影响。
南开大学筹建期间,严修、张伯苓曾于1918年赴美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私立大学考察数月,而私立大学行政管理是其十分重要的考察内容。尤需提及的是,张伯苓为此特地提前一年(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桑代克等美国著名教育学家,主修近代教育学、教育哲学等相关课程,教育行政便是其重要的主修课程[3](P59,P406)。访美期间,张伯苓专门考察了美国学校和州教育厅,克伯屈向其介绍了美国共和政体,认为“共和制度的最要原则,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之后请巴克门(Bachman)为其介绍美国学制,以及州董事会的职能和权力[4](P38-39)。张伯苓、严修还曾专门造访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南开大学因此在1923-1934年间获得该基金会持续性的经费支持。张伯苓称,“我来美国学习美国的教育体系,了解了美国精神,美国精神即世界精神”[4](P41),并在创办南开大学之时借鉴了美国私立大学董事会模式,在董事构成、权力定位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仿美痕迹。南开大学董事会负责聘任校长、募集资金、议决预算及审查决算等[5](P129)。在董事会之下,南开大学评议会具体负责校政,职权包括评议校政方针、规划校内组织、支配经费、评议校内一切建议案及重要事件[5](P129-130)。
东南大学是首个设立董事会的国立大学,校长郭秉文作为中国首位教育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孟禄。郭秉文专注于教育制度史研究,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最早对教育制度史进行系统论述,并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进行了反思和建议。孟禄对其推崇有加,认为其“不独表扬己国之事迹,且俾西人恍然有悟于中邦维新之变革。是变革也,利之所及,端在西方”[6](P5)。在东南大学建设过程中,郭秉文从理念到制度上都学习和借鉴了美国私立大学,尤其是学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管理制度。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拥有大学管理权,董事会职责包括制定学术政策、任命校长和教授、决定学校预算、监督与捐款有关事宜、指导学校管理等[7](P18)。郭秉文将中国近代教育与欧美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多次呼吁学习美国由国家、社会、学校通力合作办学之模式,十分推崇美国以社会共同参与治校为特征的外行董事会,并在陶行知等人的积极支持下筹建东南大学董事会。1921年,建校之初的东南大学董事会职权为指导校务、扶助学校(事业)之进行、保管私人捐助之财产,属于议事、咨询机构[8](P86),并不拥有大学管理权。1924年,东南大学校董会职权进一步明确为:“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审核学校预算决算;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议决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9](P117)此时,东南大学董事会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并开始拥有大学管理权,尤其是具有学术政策制定权,这与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极为相似。
南开大学董事会均由政、学、商等社会各界名流组成。1920年南开大学组成9人董事会,范源廉、严修、孙子文、李琴湘、蒋梦麟、王濬明、陶孟和、刘芸生、卞俶成等为校董,1936年国立之前的南开大学董事为范源廉、蒋梦麟、颜惠庆、丁文江、孙子文、李金藻、王秉喆、陶孟和、卞肇新等[10](P50)。东南大学首届校董有张謇、蔡元培、王正廷、袁希涛、聂云台、穆湘玥、陈光甫、余日章、严家炽、江谦、沈恩孚、黄炎培、蒋梦麟等社会各界人士17人[11](P117),其中有学界名流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有基督教领袖余日章,有商界名流钱新之、荣宗敬、穆湘玥、聂云台。同时,东南大学因其国立性质,将“教育总长指派之部员”列为“当然校董”,首届校董17人中即有教育、财政等相关政府部门官员11人,如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任鸿隽,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严家炽,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谦,江苏省公署秘书长沈恩孚。东南大学还特设“办事校董”和“经济校董”,其中“办事校董”有袁希涛、沈恩孚、黄炎培,“经济校董”有聂云台、穆藕初、钱新之,体现出董事会在社会沟通与社会合作上的作用。
除了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之外,北京师大、北京女师、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公立、私立大学也效仿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建立了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旨在募集资金并促进学校与社会沟通合作的大学董事会制度。
三、西方教会管理模式之隔空复制
随着教会书院向教会大学转型,教会大学基本形成了在西方教会主导下的“西方托事部-在华校董会”的“双层董事会”模式[12](P89)。其中,美国教会控制下的教会大学是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主导,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教会大学“双层董事会”的董事人选长期全部由西方教会指派,虽经数度调整,但仍以西方教会力量为主导。“西方托事部”代表教会利益,向教会负责,是教会大学的最高权力机关、立法中心和决策中心,掌握着教会大学的治理权和决策权,主要职权包括制定学校发展规划、任命正副校长和外籍教职员、募集资金、掌控资产等,并通过“在华校董会”实施对教会大学的管理。“在华校董会”是“西方托事部”的校务管理机构,主要负责预决算草拟、系科设置、课程审批、教职员任命、规章制定、财产管理等具体行政事务,并向“西方托事部”建议,在“西方托事部”监督和批准下,具体执行“西方托事部”的决策。
由于宗教理念和宗旨的不同,美国各派教会在管理风格上存在较大差异。比如,燕京大学由美国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等教会共同办理,燕京大学及其教会组织更愿意与中国政府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圣约翰大学所属的美国圣公会以严格出名,圣约翰大学及美国圣公会长期与中国政府保持界限,并长期拒绝向中国政府立案;沪江大学所属美国浸会却主张不涉政治。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及其所属教会组织致力于精英教育,而沪江大学及美国浸会却致力于服务基层的职业教育。整体而言,美国不同的教会组织因其独特的宗教属性而造成在教会大学管理上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由于隶属于单一教会而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圣约翰大学早期的行政组织与美国圣公会组织基本重叠,圣公会组织成员同时担任圣约翰大学管理者,可以说,美国圣公会在圣约翰大学的管理上表现出极其严格的控制权[13](P31)。美国圣公会布道部的美国总董为圣约翰大学唯一董事[14](P19)。圣约翰大学早期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华校董会”,其成员均由美国圣公会布道部会员担任,“在华校董会”会长、副会长、书记即美国圣公会布道部的会长、副会长、书记,执行委员会委员即美国圣公会布道部成员。此外,圣约翰“在华校董会”的管理权也属于美国圣公会总部。正是由于圣约翰“在华校董会”与美国圣公会布道部的组织结构一致,管理成员一致,美国圣公会对圣约翰的绝对控制权可以直接经由“在华校董会”传递到整个圣约翰。此时的圣约翰大学的董事会模式是对美国圣公会管理模式的直接复制,其功能是执行美国圣公会的校政决策。
沪江大学由美国南北浸会在华联合办理,并没有其他宗教派别的参与。美国浸会是主张纯粹、独立的民间教会,提倡民主,反对集权,反对政教合一,“教会不应涉及政治,也不要管理国家的事情”,因此浸会坚持经费完全源自民间,而独立于政府之外,甚至反对教友任职于政府[15](P3-4)。美国南北浸会坚持“学堂跟着教堂走”的精神,将其在美国本土的“教派学府”模式复制到了沪江大学管理制度中。沪江大学的决策权在美国托事部,“在华校董会”在美国托事部的指导、批准、监督咨询下管理学校,负责制定学校计划、办学政策、课程设置、经费预决算,任命包括校长在内的学校职员。根据浸会教章精神,“在华校董会”应超脱于学校行政与教学事务,因此规定包括校长在内的学校教职员不得担任董事;校长可以参加董事会会议,但没有会议表决权,并且在美国托事部的同意下行使校长权力[15](P33-35,P166)。沪江大学美国托事部成员长期以来皆为浸会成员,后来增加了如孟禄等社会知名人士,但依然保持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华校董会”成员也一直由浸会成员组成,虽然后来增加了华人董事,但浸会这种教派独立办学和独立管理的特征并未改变。1950年至1951年,沪江大学“在华校董会”由中华浸礼协会、中华浸信联会、同学会、特约校董组成,其中增加了社会民主人士为特约校董,董事构成依然突出浸会背景,保留了美国浸会“教派学府”模式的管理特征。
教会大学“在华校董会”校内权力分配上也体现出明显的教会掌控特征,这在一些教会大学在华董事实现“中国化”之后的校长权力安排上体现得十分突出。燕京大学在董事“中国化”之前,校长司徒雷登由美国托事部指派,并担任董事,拥有治校实权;而在董事“中国化”之后,校长改由中国人吴雷川担任,不再担任董事,也没有治校实权。司徒雷登依然掌握治校实权,只是此时已改任校务长。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由美国托事部指派,掌握治校权;1947年立案之后,“在华校董会”依然由主教、传教士控制,差会代表卜其吉掌握着圣约翰的行政和财政大权,华人校长涂羽卿权力十分有限。金陵大学“在华校董会”改组之后,华人校长陈裕光虽然是“当然董事”,但并无治校实权。“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个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16](P14)校长“去董事化”以及治校权被架空的现象在教会大学中普遍存在,体现出美国教会对教会大学的权力掌控。
四、近代公司管理制度之跨域迁移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上存在管理制度的“跨域迁移”现象,即一种管理模式由非教育领域迁移到教育领域,这突出体现在由商人办理并主管的学校。比如盛宣怀主持的南洋公学,其管理模式便是对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家族掌控管理模式的跨域迁移,然而南洋公学并未设立董事会制度。厦门大学筹建之初,陈嘉庚曾派人考察过外省学校,但其考查内容并未涉及学校管理,即陈嘉庚团队既未考察包括美国大学在内的外国学校管理,也未考察本土学校管理。通过考察厦门大学董事会制度与陈嘉庚公司管理模式,发现两者存在惊人的相似,一个合理的解释便是,陈嘉庚先办理近代公司,后投资办学,并自然地将自己的公司管理理念、管理模式迁移到了教育领域。
陈嘉庚公司是典型的华侨家族公司,其管理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管理权与所有权合一,保证家族对公司的控制[17](P41)。陈嘉庚公司在管理上奉行传统的家长主义管理模式,采用“创办人兼经理”的传统模式,创办人与总经理之间不设“托管”型中间环节,以强化家族公司的领导权。陈嘉庚公司各分行经理拥有分行最高决策权,有权独断分行事务[18](P5),决策过程自上而下,即“向心权威”[17](P30)。陈嘉庚公司尤其注重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和个人经验,并不太重视成文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地缘效忠更是家族公司的典型表现,在聘用公司领导层方面注重使用家族成员(包括亲家),在聘用员工方面尤其偏向选择福建同乡。
与陈嘉庚公司管理模式一脉相承,私立厦门大学董事会制度呈现出商人决策、校长集权、地缘主义等特征。私立厦门大学在建校之初设立了由校主陈嘉庚、校长林文庆、二校主陈敬贤三位闽籍华侨商业精英组成董事会,在厦门大学16年私立时期,三人董事会维系了15年之久(1921-1935年)。商人担纲、亲友组合,是私立厦门大学董事构成的重要特征。1921年的三人董事会的职权包括筹划经费、保管基金、聘请校长、审定预算、审查决算[19](P21-22),1927年增加了监查大学财务、处理其他财务事项、选任副校长之职,1933年进一步增加了议决各学院、各学系与各机关之设立、废止或变更,议决各学院、各学系讲座之设立,审定大学重要规程,授予学位等职能[20](P49)。由于陈嘉庚、陈敬贤不参与校政,董事会权力集中于校长林文庆一人之手。评议会作为议事机关,在实践中受到董事会掣肘而被架空,最终被董事会裁撤。身为“当然校董”之校长,实际上拥有无需会议讨论商议的最高校政决策权,在厦门大学几次重大人事、财政决策和多次学潮中,校长这一权力得以充分体现。
厦门大学董事会在用人上具有地缘偏好,偏向于聘用福建省尤其是闽南同乡。首届董事会的三位董事均为福建籍,首任校长邓萃英、教务主任郑贞文、总务主任何公敢等皆为福建籍。1935年改组后的厦门大学7人董事会,6人为闽籍商业精英,是厦门大学校政决策的绝对主导。厦门大学重要校董或为陈嘉庚家族成员,或与陈嘉庚家族关系密切:林文庆是陈嘉庚橡胶事业的领路人,陈敬贤是陈嘉庚的七弟,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曾江水、叶玉堆是陈嘉庚的亲家。另外两位董事黄鸿翔、林鼎礼,祖籍台湾,其家族与福建及厦门有着长期的密切关联。
陈嘉庚自小习染儒家经典,在南洋也极力主张弘扬儒家传统,在华侨中大力推广儒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传统儒家文化备受推崇,包括陈嘉庚公司在内的华侨家族公司在管理理念上都有着儒家文化的思想渊源。传统儒家强调的忠和、集权、责任,均在陈嘉庚管理理念中得到充分展现[21](P485)。具体而言,陈嘉庚不仅崇尚儒家精英主义,认为这比西方式民主管理更有效率[21](P489),还十分强调责任意识,认为一个强势且具有献身精神的领袖,是决定公司成败的关键,他本人在公司管理上也极为敬业,事必躬亲。这些理念不仅体现在陈嘉庚所创办的家族公司管理中,也体现在他所创办的厦门大学管理中。在近代众多办学者中,陈嘉庚恰恰由于其华侨商业精英的身份及其传统儒家管理理念,决定了厦门大学与众不同的董事会制度。
五、清代传统书院董事观念之近代沿袭
清代以前的一些书院已出现“学董”之称,但还未出现系统的制度文本。清中叶以降,随着书院的官学化进程,书院规条和章程大量出现,书院董事制度逐渐形成。清乾隆三十年(1766年)浙江平阳《龙湖书院章程》出现“董事”“院董”,有正、副董之分。道光以降,“董事”一词在传统书院章程、规条、规约中频繁出现,如道光年间的江苏高淳《学山书院规条》规定了董事任期、换届等事项。独立的董事制度文本也开始出现,如安徽桐城《桐乡书院章程·董事九则》对书院董事作了制度化规定,是传统书院董事制度文本的典型[22](P9)。此外,《定武书院新议经理章程》(1857年)、《石山书院首事经理章程》(1884年)也是独立董事制度文本的重要代表[23](P119)。
传统书院董事制度对董事人选及其产生方式、规模、职权等作出了规定。地方士绅不仅是传统书院的民间捐建者,而且是传统书院的实际管理者。清代传统书院董事由地方士绅民主公举推选产生,亦由地方士绅担任,山长由董事公议推举产生并向绅董负责[24](P335)。此外,有的书院董事产生方式首选传统色彩较强的家族继承方式,“董理”后裔可代“董理”之位,在无人可代之时方另行公举[25](P46)。传统书院董事会规模大小不一,少则2人,多达30人,有数可考者有2人、4人、7人、8人、10人、12人、14人、20人、24人、30人等[22](P7-8)。浙江敷文书院董事因选拔和推荐生源之需,数量竟达百人之多。书院董事总揽书院包括选聘山长、募集资金、经费管理、资产管理之职,此外还往往被赋予教学管理、教务辅助、书院祭祀等书院内部日常管理事务。事实上,传统书院董事扮演着“经理人”的角色,并由此获取固定的薪俸。随着明清书院官学化的加强,士绅沦为皇权之附庸,书院亦沦为官学之附庸,书院董事人选必须经由官方批准,书院管理行为也在官府监督下进行。虽然清代商人捐资书院并获得商籍学员名额,却由于传统的四民思想而未能担任书院董事,遑论参与书院事务决策。“士绅担纲”的传统书院董事制度由此被形塑为官府监控下的院务管理制度。清末,一些官办学校和官督商办新式学校开始以董事制度作为基本管理制度,如上海广方言馆的董事由官方指派,负责校务管理,并由此获取固定薪俸;通艺学堂董事会制度文本虽然明确了民主议事规则,且规定董事没有薪俸,但董事职权依然定位于官绅主导之下的校务管理[23](P123)。
清代传统书院董事制度关于董事负责院务管理、董事与经理概念混同、官督绅办、排斥商人入董等制度观念,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得以沿袭。这种基因沿袭并不一定或不仅仅表现在制度文本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制度实践中。也就是说,也许在制度初建之时形效美制,但在制度实践中却存在本土传承,并随着实践的展开而对最初的制度文本作出“本土化”改变。
东南大学于1920年首设国立大学董事会制度,便存在明显的官学化特征。北京政府指派官员担任“当然校董”,通过董事会掌控和干预校内学术和教学事务。政府官员历任东南大学“当然校董”,在一定程度上监控和干预校政决策。虽然在郭秉文的努力下,东南大学董事会在募集资金、学校治理、社会沟通等方面作用显著,并一度成为民国政府向全国推广的范例,却依然无法摆脱政治派系斗争的左右,终遭政府取缔。政府机关通过董事会干预校政最甚者莫过于交通大学,由政府官员和交通部官员担任的董事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董事更替亦随交通部新旧派系争斗而变动频繁[26](P92-93),交通大学董事会由此成为政治权力角逐场而匆匆落幕。在经费筹划之外,国立大学董事会往往被赋予校务决策与管理权。东南大学董事会职权从初建时的财务权扩张到教学、学术、财务、人事等所有校务,而东南大学并未明文规定董事会议事规则,造成董事会在诸多决策上缺少立法规范,极易导致校内集权。评议会被取消之后,东南大学董事会更是成为绝对的校政决策中心。
随着民族商业的发展壮大,民族资本家因投资教育而成为校董的情形十分普遍,但就整体而言,无论校内或校外、政府或民间,民国社会均难以认可商人进入大学董事会,甚至连商人因捐资教育而出任“挂名校董”之事都频繁引发校内师生的不满甚至抗议。与此同时,对于绝大多数商人而言,他们既无意参与校政,更无意建设大学,捐资教育并担任“挂名校董”,或许只为博取文化名誉和社会身份,或许是碍于情面不得不投资,又或许是为了亲友子女获取教育资源。通常情况下,近代民族资本家深受传统观念和投资环境的影响,其教育投资行为往往不具可持续性。不论从主观抑或客观而言,民国时期捐资大学的民族资本家与清代捐资书院的商人一样,普遍具有“投资非治理”的角色定位,往往被排除在大学治校权力之外。
六、权力博弈之下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变迁
制度的多重来源决定了制度模式的多重样态和多元特征。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先后出现了传统书院模式、教会控制模式、美校模式和近代家族公司模式等不同来源,由此形成了多重制度样态。交织着政权、教会、社团、学者、商人等不同办学主体的治校权力博弈,在国内民族主义运动、国内军阀战争、世界经济大萧条等因素的影响下,民国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经历了多次制度调整。
不同的办学主体不仅直接影响了对董事会制度模式的选择,更决定了董事会的权力归属,这也是引发治校权力博弈的根本原因。教会大学多由西方教会创办,作为办学主体的教会选择了既适合学校办学又能够全面控制学校的教会控制模式。私立厦门大学由侨商创办,作为办学主体的侨商确立了自己熟稔并具有“向心权威”的近代家族公司模式。私立南开等校由留美学者和社会各界名流共同创办,作为具有留美经历的学界名流确立了外行治理、社会沟通功能的美校模式。国立东南大学由民国政府准予创办、东南社会共同建设,在引进美校模式的同时,又深受其国立性质之左右。
随着民国政府对立案规范和教育权力的逐渐强化,大学董事会发生了制度转向。教会大学双层董事会先后发生过三次制度转向,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大学治理权由“西方托事部”转向“在华校董会”,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治理权由西方人士为主转向以中方人士为主,全面抗战前后治理权由西方教会转向中国政府[12](P89-96)。在这场与中国政府的治校权力博弈中,西方教会的治校权力不断遭遇削弱,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完全被排除在中国教育体系之外。一些国立、私立大学董事会虽然效仿了美校模式,吸纳社会力量共同治校,但基于中国国情,董事以政界、学界等传统社会认可的名流为主,商人、军阀依然受到传统董事观念影响而遭遇排斥。传统书院董事制度的“投资非治理”观念依然存在,投资者的办学投资行为往往是短期性的而非持续性的。翻版自近代公司管理制度的大学董事会制度较为罕见,在传统观念以及模仿美制的影响之下,难以获得民国社会的普遍认可。陈嘉庚家族公司为确保对厦门大学的主导权而表现出管理权与所有权合一,并在南京政府要求改组之下依然保持着家族公司的管理特征。然而,厦门大学由于办学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其发展完全受制于公司经营状况,当陈嘉庚公司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巨大冲击而陷于停滞之际,厦门大学经费便难以为继,国立化成为必然选择。
南京国民政府在取缔国立大学董事会之后,参照美国校董会模式,通过颁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私立学校条例》《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私立学校规程》《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等系列教育法规进一步明确私立学校及其校董会的立案条件。《私立学校规程》(1933)规定,校董会为“设立者之代表”,设立者为当然校董;校董名额不得超过十五人;限定“校董会至少须有四分之一之校董,以曾经研究教育或办理教育者充任,现任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及其直接上级教育行政机关人员,不得兼任校董。有特别情形者得以外国人充任校董,但名额至多不得过三分之一,其董事长须由中国人充任。”[27](P141-143)《私立学校规程》(1933)不仅要求部分校董应由懂得教育之人担任,而且杜绝了教育主管部门官员担任校董的情形。同时明确校董会职权,包括选聘校长、筹划经费、审核预决算、保管和监察财务,不得参与校政。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通过出台《改进高等教育计划》《限制宗教团体设立学校令》《学位授予法》等系列教育立法,从系科设置、宗教课程、学位授予等方面对校董会进行规约,并以此作为学校向政府立案的基本条件,私立大学、教会大学董事会不得不遵章改组以获得政府的立法支持,谋求学校之发展。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教育立法,使大学董事会制度从多样逐渐趋于统一,逐步确立了近代校董会制度的基本形态,并在与不同办学主体的权力博弈中加强了政府对大学教育的主导。
注释
①广义上的私立大学包括了西方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以及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狭义的私立大学专指由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本文所指私立大学为后者,以示区分。
参考文献
[1][美]亚瑟·M.科恩,卡丽·B.基斯克.美国高等教育的历程(第2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2][美]亚瑟·科恩.美国高等教育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4]龚克.张伯苓全集·张伯苓年谱(第十卷)[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5]南开大学章程(1932年)[A].梁吉生.南开大学章程规则汇编(1919-1949)[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6]孟禄·序二[A].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7]冒荣.至平至善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8.
[8]朱斐.东南大学史(第一卷)1902-1949[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9]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简章(奉中华民国13年6月25日教育部指令修正)[A].《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南开大学创办人、校董及教职员一览表(1936年)[A].王文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11]东南大学第一次校董名单[A].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任小燕.晚清和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双层董事会”的制度转向[J].高等教育研究,2016(10).
[13]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4]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1917.9-1918.7)[Z].上海:美华书馆,1918.
[15]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6]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A].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17]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18]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民国十八年)[Z].厦门市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案卷:陈嘉庚公司分行关于民国十八年公司分行章程(二)(1929),档号:A003-1929-A03-Y-0002.
[19]厦门大学大纲(1921)[A].黄宗实,郑文贞.厦大校史资料(1921-1937)第一辑[Z].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20]厦门大学组织大纲(1933)[A].黄宗实,郑文贞.厦大校史资料(1921-1937)第一辑[Z].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21]颜清湟.从历史角度看海外华人社会变革[M].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22]邓洪波.古代书院的董事会制度[J].大学教育科学,2011(4).
[23]任小燕.清代传统书院董事制度及其流变的历史考察[J].教育学报,2016(6).
[24]朱汉民,邓洪波,高峰煜.长江流域的书院[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5]任小燕.博弈中的生存: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26]任小燕.“自治”抑或“他治”?——民国时期公立大学董事会制度性质的历史考察[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27]私立学校规程(教育部1933年10月19日修正公布)[A].宋恩荣,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版权声明
本微信公众号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官方微信,如无特殊说明,本微信内容均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期刊,版权所有,欢迎转载。
本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刊声明
一、《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不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任何费用,也从未委托过任何人或组织代为收费组稿。如有个人或组合假借我刊名义收费,均属诈骗行为,须承担法法律责任。希望广大作者和读者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投稿指南:
教育史 高等教育:
gaoxiaoli67@163.com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zongjianmei@126.com
教师与教师教育:
huyanhua11@163.com
国际与比较教育:
jianghuili0512@163.com
课程与教学论 学前教育:
huosujun08@163.com
教育理论及其他:
jiaoyub@hebtu.edu.cn
三、有关事项可电话咨询:教育科学版:0311-80786366 编辑室办公室:0311-80786360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平台编辑:赵玉杰
审核:谷更有、孙秀昌、高小立、姜惠莉、胡燕华、霍素君、宗健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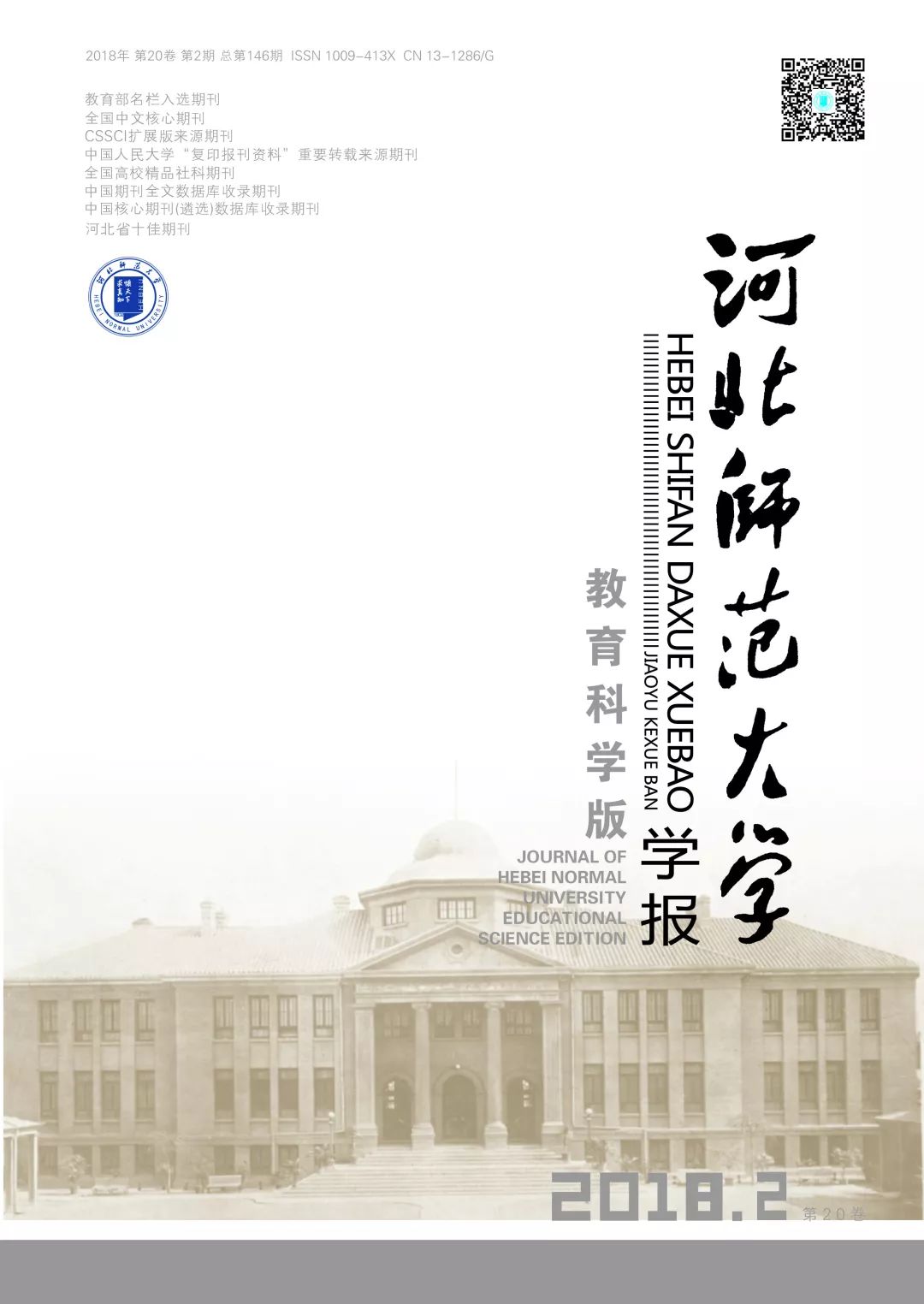
河北师大学报
教育科学版

微信ID:hebeishifandaxuexuebaojiaoyukexueban
网址:xuebao.hebtu.edu.cn
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