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冬天,受英国好友巴夫勒尔邀请,德莱塞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欧洲之旅,先后游历了英、法、摩纳哥、意大利、梵蒂冈、荷兰、德国、瑞士和比利时。这本书生动再现了上世纪初欧洲的社会、艺术和人文风貌,读者除跟随德莱塞一路游览名胜古迹外,亦可不时读到他对个人命运、民族性格、社会变革等诸多深刻话题的独特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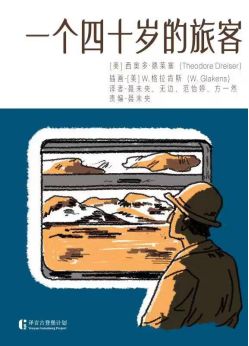
在书中,他以美国人的视角,打量欧洲,形成了着实有趣的观照。他描写自己在伦敦上流社会人家做客,教站街女莉莉美式俚语,在摩纳哥赌场输钱,在巴黎出入浮华场所,在意大利威尼斯与神秘女子玛利亚夜游,在罗马追随当地导游坦尼先生,在德国的小镇马延寻访当年父亲因偷吃樱桃被打的故居,等诸多经历,笔触诙谐生动,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他善用白描,寥寥几笔就勾画出偶遇的农民、小贩、收藏家、艺术家、神父、女演员、推销员、导游、日本游客、鸡肉商夫妇等众多人物形象,令人难忘。本书使人充分感受到德莱塞对生命的热爱;其中更渗透着人性的观察、文化的碰撞,引人深思,使人感受到他深邃智慧的另一面。
《一个四十岁的旅客》是美国现代小说先驱西奥多·德莱塞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首次在国内译介出版。在这本散文游记中,德莱塞传递给我们的对人性和社会的洞察丝毫不逊色于他的任何一部小说。
作者简介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年8月27日-1945年12月28日),与海明威和福克纳,并称为美国现代小说三巨头。代表作有《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金融家》、《巨人》、《天才》和《美国悲剧》。
德莱塞拥有许多忠实的追随者,其中不乏与他同时代的舍伍德·安德森等名家。辛克莱·路易斯和多斯·帕索斯也认为德莱塞为他们创作开辟了道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甚至誉称德莱塞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人物。
1930年路易斯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词中,向全世界昭示了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伟绩。作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美国作家,路易斯认为德莱塞才是荣膺该奖的更佳人选,他说:“德莱塞常常得不到人们的赏识,有时还遭人忌恨,但跟任何别的美国作家相比,他总是独辟蹊径,勇往直前,在美国小说领域里,为从维多利亚时期和豪威尔斯式的胆怯与斯文风格转向忠实、大胆和生活的激情扫清了道路。没有他披荆斩棘开拓的功绩,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哪一位——除非他甘心情愿去坐牢——敢把生活、美和恐怖通通描绘出来。”
精彩段落
我刚刚踏入四十岁的门槛。也算见过一些世面。当记者,做编辑,给杂志投稿,写书,这之前,在没搞清楚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之前,我还做过各式各样的小职员。
十一年前,我写了生平第一部小说,交给一个纽约出版商出版,后来却莫名其妙遭到他的打压,天知道为什么。因为就在他们宣称我的书有伤风化而停止发行的同一年,他们出版了左拉的《繁殖》和《一个英国女人的情书》。
十一年来我始终都很不解,如今我想明白了,与其说因为所谓的道德问题,不如说因为这本书对美国整体生活真实而坦率的描述,这一点,在当时还不为人们所接受。在当时的美国,我们还不习惯实话实说,特别是在书里。我们隔着时空,向托尔斯泰和福楼拜还有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这些巨擘致敬——我们有些人——并且不无炫耀地把他们的书成套摆上自家书架,但在文学上,我们主要还是受教于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查尔斯·兰姆,还有英国感伤现实主义者的精致陪伴,从中我们了解到生活的某些方面,但不是全部真相。
毋庸置疑,这些伟人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千疮百孔——充满着谎言、虚构、幻象和欺诈,但他们似乎普遍达成共识,或为迎合公众,或为着某种情结,对此避而不谈。书籍总是基于“我们更好的本性”来构思创作。我们总是展示我们希望被看到的那些方面。
这世上肯定有坏蛋——骗子、无赖、小偷、流氓,但他们是稀有动物,隐藏在黑暗的人迹罕至之处,除非在黑夜中才会偶尔撞到;而所有我们这些正派、聪明、诚实、善良的人们,生活在美好的家园,走着自己的正直诚实之路,去教堂,养育孩子,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犯错,除非那些骗子、无赖、小偷等等突然出现,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的书大多把我们描绘成英雄。如果我们的女儿们出了什么事,那也不是她们的错,而是这些卑鄙坏人的错。我们大多没有原罪。我们的书,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法律,还有我们的监狱,意在确保这一点。
我确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以一种朴素、直接的方式来理解生活,真的是一种进步。拿我个人来说,我现在就不接受任何信条。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什么是爱,什么是希望。我不绝对相信哪个人,也不绝对怀疑哪个人。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善恶集于一身的。
一天早上,我打开邮箱,意外地发现了一张送到我公寓来的便条,现在看来,这张便条很有纪念意义。这是我一位英格兰文学界的朋友写的,他留言说急于见到我。我一直很喜欢他。我喜欢他,因为他有趣的英式风度,他对于文学和艺术有着鲜明独到的个人观点,而且他广有智慧,品位不俗,才华出众。他右眼戴着单片眼镜,就像理查德·张伯伦,这一点我也喜欢。我喜欢那些仪态高贵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否喜欢我,尤其当高贵的外表有真实的人格做支撑时。巴夫勒尔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天早上,巴夫勒尔和我共进早餐;没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事儿了。他来晚了——很晚。他高视阔步,鞋罩锃亮,单片眼镜闪烁着,后面是一只敏锐的、探询的眼睛。他整个人看起来态度和蔼,怡然自得,一副发号施令说了算的派头。对于他感兴趣的事,在各种情况下,他都可以迅速占据主动,轻松搞定,安排妥当。
“我已经决定了。”他以管理者的姿态说。他的这种态度,总是让我感到开心,因为我骨子里最缺乏管理世事的能力。“您和我一起回英格兰。我已经安排好二十二日的航程。您在英格兰先到舍下;在那里盘桓几日;然后我带您去伦敦,找一个好旅馆住下。您将在那里呆到一月一日,然后我们一起去法国南部的尼斯、里维埃拉、蒙特卡洛;从那里您去罗马,去巴黎,我会在巴黎与您会合——然后在春天或夏天,等完成笔记,您再返回伦敦或纽约,把旅行印象写成一本书,我保证会出版!”
“如果能这样安排。”我插嘴道。
“能安排,”他强调,“我负责张罗相关费用,我会接洽一家美国出版社和一家英国出版社。”
有时生活真的会大发善心。它走进来,说,“嘿!我想让你做件事”,接下去它为你安排好一切。这一次,我感觉非同寻常,好像我正处于一种临界状态,而我的生活即将发生巨大变动。如果一个人在二十岁面对人生中首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他将何等兴奋,但是当他四十岁时,他更多的会想到前路吉凶莫测而忧心忡忡。
很长时间我都没法忘记开船那天的情形。一大早我们驱车行驶在市中心,我在一份晨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我的一位朋友自杀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男人。他陷入了困境;妻子也抛弃了他;他负债累累。我和他很熟,了解他那些飘忽不定的经历。就在这个清晨,正当我启程游历欧洲,俨然取得了一场文学上的短暂胜利,他却倒地死去。这使我犹豫了一下。
我想起了那句拉丁语, “memento mori”。我再次意识到,就在此刻这一片光明的核心深处,生活其实多么严酷。命运是仁慈的,抑或恰恰相反。它推动你向前,或者正好相反。如果它没有站在你这一边,那你就彻底没救了。我承认复仇女神的存在。我相信她们。我已经听到她们扇动翅膀时那毁灭性的击打声。
等我到了船上,已经是一个完美的阳光灿烂的早晨。太阳高照;海鸥成群飞翔;一种美妙而新奇的旅行氛围笼罩着第十三街脚下的邮轮码头。
是否有初次登船的小男孩,像我一样,面对这海上巨兽,激动地浑身战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