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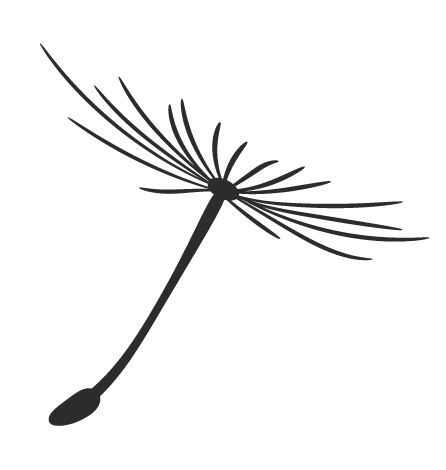
一把刀子(二)
前情提要:茶花被湖和稻子收留,湖始终对身边人温柔,稻子却仿佛对茶花有敌意。他们的城市正在死去,这是一个不能公之于众却人尽皆知的秘密。茶花对这一切并不陌生——她曾经见证了一个小镇的死亡。茶花到底来自何处?她有怎样的故事?
贰、无法承受的宽恕
一阵漩涡般的深眠后,我从平静的黑夜中央突兀醒来。
细碎的、愈加急促的呼吸声传入我的耳朵,撩拨我的神经。我一时之间竟不能分辨那是否是我自己发出的声音。
我听到雨水被山谷吞没的静寂、花开花落的脆弱音绊和喑哑纷乱的树响。这些声音像绳子一样缠来绕去,将我魇住,将我捆绑。
隐隐约约地,好像有人在唤我的名字。
每一个字,都是从肺里吐出,尽量放得低缓,尾音拖得又轻又沉又绵长。
茶——花——茶——花——
嘶哑而模糊。叫人听不出表情。
茶——
断断续续。呼吸戛然而止。
花——
我有些害怕,用被子蒙住头。冷汗浸湿了床单。
茶——花——
是谁呢?我在脑海中迅速搜索。
“噔。”紧绷的神经清脆地断裂。像一把古老的琴、那已无法修补的弦。
卤花婆婆。
我知道是您。

“可怜的孩子,慢一点吃。”油亮的圆木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疙瘩汤。啊,汤上浮着几叶香菜,几缕飘舞的蛋花和形状美好的西红柿。卤花婆婆就坐在近处看着我狼吞虎咽。
滚烫的小面块轱辘轱辘地滚进胃里,发出动人的咕噜咕噜声。
“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花’字,说不定上辈子是祖孙呐。”卤花婆婆高兴地说着。而我,只顾呼噜噜地吃,并不仔细听。
“你不要再流浪了,茶花。以后,你就住在莺镇,跟我一起住。”
我吞咽的动作停滞了,眼光钉在氤氲的热气中,被佐料的香味硌得生疼。
“来,作为这个家的新成员,认识一下‘麒麟’。它也曾是一个流浪儿。”一只褐色瘸腿猫歪歪扭扭地跑过来了——嚯,就这烂猫,叫什么?“麒麟”?我在心里窃笑,但表面上掩饰住了鄙夷的神色。
猫儿似乎洞穿了我的心思,略带敌意地大喵一声,以示恐吓。
我连忙咽下还迟迟含在口中的食物。

那时的小镇还没有变成死城。那时的莺镇那样安宁。阡陌交通,民风淳朴。低矮的房屋,泥巴糊的土墙,有一些残破的瓦片半埋在泥土里,伴着整日影影绰绰的细柳。波光粼粼的河面,有暖融融的阳光照在结构简单的木船上,岸边的孩童爱赤着胳膊捉浅滩里静默的虾。大地上零散的人家,鸡犬相闻;田里的麦穗,鸟语花香。
镇中心有一条长长的市场街,卖熟食,卖水果,卖烟酒糖茶,卖锅碗瓢盆,卖各种各样的吃食和杂货。叫卖声从早到晚,讨价还价声很吵闹,但人情味饱足到让浸身其中的人们涨红双颊、心醉神迷。
卤花婆婆靠打渔为生。她有一张潮湿而咸涩的鱼网和一只破旧却温柔的鱼筐。她用这两样东西养活我和麒麟。有时是我去河里网鱼,再由卤花婆婆拿着装满鱼的鱼筐到市场上卖,有时卤花婆婆腿痛或者眼睛痛,就是我一个人网鱼,再一个人去贩鱼。麒麟则终日睡懒觉。
那时的莺镇四季也不完整——那里也没有冬。
可是后来冬来了,便无论如何也驱赶不走。陌生而残酷的气氛杀死了这座小镇。
很多人离开了。很多人死了。麒麟也失踪了。死城里只剩下我和卤花婆婆。

卤花婆婆视力本来就弱,在灰蒙蒙的白日里再不能坐到她心爱的纺车前摇着粗陋的把手,有秩有序地纺出一张张长纱,也再不能给我此刻受冻的脚纳一双新鞋。她只是日复一日地提着一盏熄灭的灯笼,幽灵一样在死城里四处游走,寻找食物。有时天色更阴,卤花婆婆完全看不见东西,却还是偏执而盲目地走,步伐越来越蹒跚,像一个趔趄打得异常厉害的提线木偶,弱不禁风,左右前后地摆动。直到她的鞋底磨穿了,冰冷的青石板开始与她苍老的双脚实在地接触。我很耽心,怕她的脚渐渐磨光,磨到小腿,磨坏膝盖,最后卤花婆婆会成为一个只有半截身子的老人。
果然,她的双脚磨得不住地流血,脚底板脱落出肉沫。但事实上,她的脚还未磨蚀掉,她就死了。

卤花婆婆在河岸边毫无征兆地倒下去,像个单薄的纸人。纸质的灯笼被扯出一道伤口,洒出几粒旧到斑驳的灰烬。这是死城的最后讣告,也是卤花婆婆留给死城的遗物。
河水已成死水,没有生命的痕迹。黝黑的水。没有波纹,没有气味。没有生命。
卤花婆婆固执地翻过身,匍匐着,已不试图要支撑着手臂站起来。僵硬的身体奇异地扭动,像一条垂死的蜈蚣。她的影子压在腹下,微微地颤抖。她爬回我们的房子,趴到门口,扒着门槛,用叹气般的声音叫我:茶花、茶花。

我慌忙摸索到门边,跪在她面前,像在等待神圣的祝福。
卤花婆婆急切地拉着我,枯死的指甲嵌进我的衣服。望着她那皱缩的面庞上露出惊人的战栗,突然惧怕极了,但我又有义务跪在这里,不能躲,只好始终眼巴巴地望着她,盼她说话。她粗粝的嘴唇圆圆扁扁,仿若鱼在用腮呼吸,睁圆的眼睛放射出无与伦比的光彩。
我侧耳俯身,凑近了听。
“茶花,我知道你都干了什么。我原谅你。”
深奥莫测的审判。
我都干了什么?我都干了什么?我的身体里传出马蹄铁徜徉的律动——那是我惊恐的心跳。我都干了什么?卤花婆婆知道什么?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我做过的事?
我不知道。所以我无从争辩。
再看卤花婆婆,明亮的眸子永久地凝固了,灰色的指甲依然牢牢嵌在我的衣服里。话像是宽容,死去时的动作却像要把我拉进地狱。
我的背根觉察出瘆人的阴冷。这一切有多么恐怖。
我狂奔起来。

卤花婆婆的尸体紧跟着我。褴褛的衣衫拖在地上沙哑作响。我捂住耳朵拼命尖叫,仍遮不住粗糙的磨擦声。终于,我跑到卤花婆婆倒下的那个岸边,使劲掰开她的手,一鼓作气将僵硬的尸体推入漆黑的死水。
长吁。
我转身,背对着死水,环视冬城孤村。
倏尔间哀毁骨立。
我都干了什么?让我好好想想。

茶花——茶花——回忆盒子很潘多拉,说合上就合上。
我瞪着天花板,周围已经捕捉不到呼唤声。方才像是一场梦。如果真是梦,应该付之一炬,烧个干净。
窗外的夜幕,弯弯月牙若隐若现,像达芬奇笔下奇特的韵染法所勾勒出的蒙娜丽莎的微笑。雾霭安详。我想,这总比没有月亮要好,于是心情便宁谧下来。
东方渐渐泛白。
就算死之前的回光返照,明天也定能看到亲爱的太阳。
我放心地闭上眼,朦胧睡去。
下节提要:稻子约茶花去皮豆餐厅,她们会吃到哪些诡异的食物?茶花到底做了什么呢?她在害怕什么?莺镇的死亡与诞城的将死有没有关系?敬请关注《一把刀子(三)》。
文章:熊小姐爱吃白菜
编辑:哭唧唧的方大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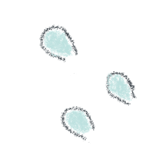
一想到你在关注我就忍不住有点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