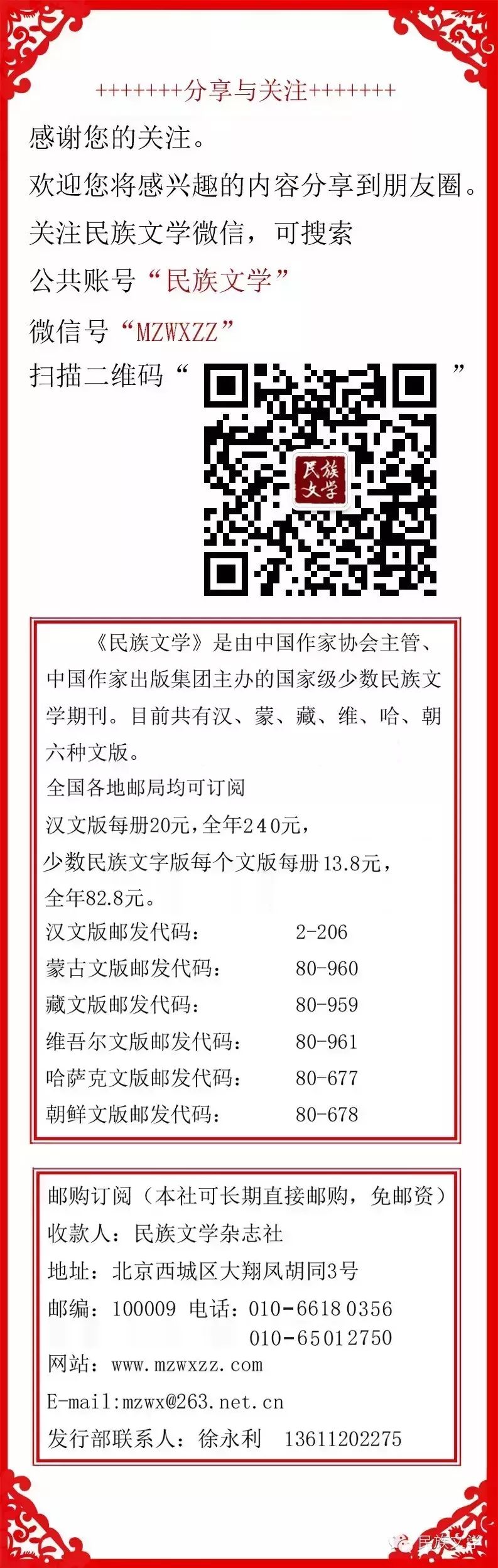点击上方“民族文学”可订阅哦!

谨以此文,献给香港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推普工作者。
——题记
香港,是一个奇特的地方,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这里,有的短暂停留,有的如候鸟栖居,大多数人在这里扎下根来,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有人说,香港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作任性,夏天穿羽绒着高筒靴招摇过市,冬天穿迷你裙吊带背心穿街走巷,没有谁会多看你一眼,更不会因此而皱一下眉头。每一个人都是微小的个体,没有人会在意你,一不留神,分分钟便被淹没在那些迎面而来的巨大冷漠洪流中;也有人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只要你勤奋、肯捱苦、愿意努力,机会它无处不在。在这座城,任何时候,只要不违法,你都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过活。
香港,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被英国殖民一百五十六年后,1997年回归祖国。人口七百四十八万,面积一千一百零六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世界第一。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港经济高度发达,人均GDP排名全球第十、中国第二,医疗健全、教育优质、物质富足、商业娱乐业发达;香港男性平均寿命全球第一,女性排第二。据资料记载,十九世纪初,香港只是一渔村,仅有五千至七千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远攻清廷,女皇原本下令抢占舟山,但前线将军路过香港时,发现这里,地理优越,水深港阔,未来潜力无限!于是将军不惜惹怒女皇,调头强占了香港岛。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割让英国。这一“偶然发现”,彻底改变了香港的历史。凭借海港优势,香港这个自由港,发展成了今天的“国际大都会”。
二十多年前,来到这座举世闻名的城,当我穿梭在香港如织的人流中,往来行走的多是中国人的面孔。他们穿着简单时尚,行走如风,自信满满,满口粤语方言还不时夹杂着一句半句英文,在街上你用普通话问个路都有困难。他们听不懂,也不会看简体字,就算听明白你说什么,人家回答的你也是听得云里雾里,在这里你就觉得自己是个异类,无法插足,无法融入。香港自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大部分政府文书都用英文,英文亦长期是唯一法定语文,中文没有宪制地位。回归二十年来,香港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香港政府大力推行两文三语——中文、英文,粤语、英语、普通话。语言环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与一群默默奉献的普通话教师有着莫大的关系。多年来,我无数次有这么一个想法,写写我身边教普通话的朋友们吧!写写他们的背井离乡,写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写写他们的苦难幸福,写写他们的从容与慌张,写写他们的坚持与放下;写写他们从一个又一个的远方奔向此处,写写他们从各自安静或不安静的世界来到这座喧嚣的城市,写写他们作为新移民的体会和感受,写写他们在这里怎样艰辛又努力地工作着、生活着、生存着。
当我终于付诸行动,开始倾听一个个他(她)讲述的故事,有时安静默然,有时相对而笑,有时拍案叫绝,有时击台而歌,有时泪流满面,有时紧紧拥抱……在这片曾被殖民一百多年的土地上,在港人的国家认同感还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推广普通话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而正是我身边这样一个普通的群体,在推广普通话以及去殖民化的道路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心血,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辛酸,各自的精彩,各自的妥协,各自的坚守。我用笔,为这个群体向世界打开一扇窗,希望,明媚的阳光能照见它,清朗的月亮能照见它,照见这一扇边沿角落的窗,照见一个个默默发光的人。
一
“这一刻,很多故人涌出来,很多故事涌出来,经历的时候只是经历,经历过后就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而很多的故事串起来,就是人生。”
清早时分,从九龙至香港岛,出了地铁站,穿过湾仔老街各式热闹的店铺,爬上一道斜坡,与许维琳老师约见的“金兜记”酒楼终于出现眼前。
湾仔,位于香港岛北岸中央位置,是一个新旧并存的独特社区,糅合旧传统与新发展的精粹,亦是香港历史最悠久和最富传统文化特色的地区之一。许老师就住在这一区,平日喜欢到这家存在了几十年的港式酒楼喝早茶。在香港,人们有喝早茶的习惯,俗称“饮茶”,早茶主要由中式点心和茶水构成。
许维琳老师,香港最早的普通话倡导者及传播者之一,六十年代到港之后,一直从事普通话教育、组织及评审工作,多年来,教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扶持了一批又一批的后辈,帮助了一间又一间机构,与她有关联的普通话机构多不胜数。
与许老师初识于十几年前,我作为某校的课外朗诵辅导教师,带着几十个一年级的孩子去参加全港校际朗诵节集诵比赛,许老师是评委,那是我第一次带集诵。香港学校的音乐节及朗诵节,是学界瞩目的文艺盛事,至今已走过七十个年头,这是让热爱音乐和朗诵的青少年得以一展所长的独特平台。倡导人之一许维琳女士,自1968年开始到2018年退休,整整五十年时间,从最初不为人知,参加者寥寥无几,一点一滴积累,影响逐渐扩大,到今日全港学校参与,人人以获其奖项为荣,甚至升读本港名校亦以此为加分条件。在民间大大小小不同比赛,论规模校际朗诵节应可称冠,这与许老师对此项朗诵文化艺术教育多年来前前后后亲力亲为,努力推广分不开,若说她功不可没,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记得那场比赛是在冬天,海风刺骨。在尖沙咀某比赛场地,学生们穿着厚厚的羽绒外套,笨拙地爬上朗诵台的阶梯,我微笑着等他们站好,准备转身回座位坐下时,赫然发现第一排的一个小胖孩没拉上外套拉链,重点是他的裤子拉链也没拉上!台下已经传来一阵嬉笑声,有的小孩竟然直接指着他嚷嚷:喂,你的大门没关上!小胖学生意识到大家在笑自己,低头一看,动作夸张地马上将裤子的拉链拉上,还冲着台下伸伸舌头“嘿嘿”一乐。台下更是笑翻了,整个比赛场地乱成一片。我的脑袋“轰”地一下,这还用比吗?两个多月的训练白费了!按照朗诵比赛的规定,肯定没奖了!
许老师按了几下桌前的响铃,现场慢慢安静下来。她接着又按了一次,示意比赛开始。天真可爱的学生们似乎没有受影响,依照平日的训练,表情投入、有感情,动作也整齐协调,演绎完毕孩子们有条不紊地按照我的嘱咐分行离开舞台。台下的掌声很热烈,许老师的表情似乎也很满意,我内心里那个悔呀!怎么事前就没有好好检查一下这群“小猴子们”的衣着呢?按正常评分标准与之前比赛的队伍来看,我的学生表现不俗,应该是能够获奖的。但比赛前发生的那个小插曲,肯定会大大影响比赛的得分。
最后一队比完后,评判助理请主评判上台宣布获奖名单并点评朗诵作品。穿着很有品位的许老师缓缓走上台,先由朗诵作品说起,给大家讲解作品及作者背景,其内含的深意;在表现作品时,哪一段该强哪一段该弱,哪一段该快哪一段该慢,哪里该适当以动作辅助,哪里该用眼神深刻体现,她一面讲一面示范,给在场的学生和老师们上了极其生动而难忘的一课。
在宣布奖项时,她手拿评分纸,看了看台下,所有人都屏息静气,等待这激动人心的结果。许老师却不着急公布,不紧不慢地说:孩子们,是不是很希望听到你们学校的名字呀?台下齐齐回答:是。许老师又问:要是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会难过吗?台下的孩子们老老实实地回答:会。许老师笑了,她说:会是正常的,不难过是假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辛苦训练,有谁不希望能够拿个大奖回去!这对学校对老师对家长对自己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交代。但是比赛的队伍这么多,竞争这么激烈,而奖项又有限,怎么办呢?学生们天真地回答:那就给多一点奖呀!许老师笑着说:如果我像圣诞老人分派礼物那样,人人有份,永不落空,那比赛还有没有意思?说真的,看着你们在台上的表现,看你们如此全情地投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感动,你们已经懂得齐心合作的重要。我想,在比赛中初尝荣光、挫折、友谊、合作、坚持的滋味,因着不同作品和对手,力求个人的进步,这一些,比奖项更重要。
看着台下孩子们一脸懵懂的样子,许老师又笑着说:我的意思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有了不一样的经历,学会了友爱、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只要这个过程是快乐的、享受的,那就是你们最大的收获,这比获奖重要多了!
许老师开始宣布获奖名单,按照惯例,季军有三队,亚军两队,冠军一队,比赛队伍有三十几队,所以要从中脱颖而出很不容易。在公布了前两队季军获得者后,许老师忽然说:今天有一队学生,整体的朗诵表现不俗,按照我的标准,他们原本是可以获得冠军的。我的心“咯噔”一下,不会是说我们吧?她继续慢慢说道:遗憾的是,他们在上场后出现了一些状况,按照比赛规定应该是没奖了,但他们的朗诵无论是情感、动作、整体的合作方面,都实在是让人赞叹的!指导老师对作品深刻理解,对学生的细心辅导,再加上孩子们齐心配合才会有这么好的表现,所以今天我破例给他们一个奖项,以资鼓励。但老师们今后一定要注意,学生上台前的着装、仪表一定要确认,只要上到台上,就不能再有任何小动作。另外比赛前可以脱掉笨重的羽绒服,不然孩子们都成笨重的小企鹅了!
全场人都笑起来,在笑声中许老师读出了我们学校的名字,孩子们都乐坏了!学生代表上台从许老师手中接过评分纸和奖状的时候,我的内心涌起无限感慨!我是何其幸运,第一次带集诵就遇到这么好的评委老师,短短三个小时,她不仅教会了我不少专业上的技巧,更让我体会到超越小我的爱与情怀。
十几年过去,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常常会见到许老师的身影,我总是怀着崇敬而欣喜的心情前去打招呼。此刻,她正坐在“金兜记”的角落里,安静地等着我。
见我来到,许老师起身热情招呼着,依然是得体讲究的衣着,亲切而不失分寸的笑容,恬淡谦和的神情,让人忍不住就想亲近她,听她暖暖地说话。她拉着我的手仔细看了一下说:好久不见,还是那么漂亮。说得我心里不禁乐开了花,定力还是不行啊!我也由衷地说:许老师才是好看,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如此优雅得体。许老师笑了起来:哈哈,别哄我开心,我都八十岁的人了,哪里还会好看。八十岁?怎么可能!您就是六十多岁的样子啊!许老师敛起笑容,认真跟我说:对,八十岁。我1939年出生,今年刚好八十,也正式宣布退休了。一直活跃于香港普通话界以及教育界的许老师,行至耄耋之年才宣布正式退休,如此敬业乐业,这让我的内心更是升起无尽的敬意。
许老师感慨地说:“日子真快呀!那天看家里的各种奖牌,发现自己竟然跟那么多普通话团体都有关系,我的一生就是这么忙忙碌碌的,一转眼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今年不知怎么了,一些早已失去联系的故人都出现了,忽然一个个又回到自己身边来。
“我1961年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1962年到的香港。当时内地已经批准出境,但香港却拒绝入境,因为香港政府怕大量的内地居民涌入香港,所以开始限制入境人数。当时先生已经先行到了香港,投奔解放前就到香港去的父亲,他们在香港开了一个小工厂,过着还算稳定的生活。公公婆婆一直叫我带着孩子到香港团聚,没有入境证明,于是只有到广州某个码头偷渡。
“大年三十那天,交付了八百块钱,八百块钱在当时工资只有几元的年代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带着孩子满怀忐忑地和一群陌生人一起上了船。当船驶离码头的时候,我的内心真是百种滋味交织,既担心遇到飓风搞得船毁人亡,又害怕被海上缉查偷渡的警方抓获,一个会没命,一个会损失惨重,都是难以承受的事。但为了一家团聚,也只能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了。漆黑的夜里,船行驶到一半,海浪越来越高,越来越汹涌,海水把身上的衣服都打湿了。坐在简陋的渡轮上,船身一会儿随着海浪抛到高处,一会儿又被甩向低处,人也跟着船被抛上抛下。我晕船晕得不行,呕吐得非常厉害,还要紧紧抱着孩子,那种滋味,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仍然心惊胆颤。当时船上有一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看我孩子身上穿着印有“爱和平”字样的衣服,善意地提醒我说这衣服不行的,香港警察一看到“爱和平”的字眼,就知道你是内地来的,一上岸就会被抓走。我的内心又多了一重恐惧,如果千辛万苦到了香港,上了岸还因为一句“爱和平”又要被抓走遣送回内地的话,岂不前功尽弃?但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多余的衣服让孩子换,唯有冒一次险了!
“去到海那边,接应的先生带我们迅速上车离开,总算是有惊无险,平安偷渡到了香港。公公、婆婆很高兴,年初三便邀约朋友吃饭,而被邀的朋友家庭中,竟然有那个年轻人。他一见我们,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哈,那个‘爱和平’的小孩竟然在这里!这位朋友是位导演,在台湾拍了不少电影。今年,有相识的朋友相约,与从国外回来的他到城市大学喝茶。五十几年后,看到我那如今已快六十的儿子,他再次哈哈笑着说:当年那个爱和平的小孩,都已经变成老头子啦!我们更是老人中的老人了,岁月不饶人呐!这人生兜兜转转、兜兜转转,真的很有意思。”
刚到香港的时候,许老师一下子找不到工作,内地又回不去了,一时间也是有些着急。后来又因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历不被当时的香港政府承认,便到香港珠海学院学习两年,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前夕,学生会的负责人找到她,邀请她在“双十”节搞一个演讲,并暗示她这不只可以让她“名利双收”,而且毕业找工作也会事半功倍。她想都没想便严词拒绝了这个邀请,尽管来到香港,但自己仍然心系祖国,也一直热爱和平,不会去做任何分裂祖国的事情。事后许老师以为得罪了这位负责人,肯定会给自己小鞋穿。没想到不但没受到影响,她的正直勇敢及爱国的热情反而让对方对自己刮目相看。不但关心她的毕业问题,更介绍她到当时唯一一家“国语”教学的名校当小学教师。因为在内地学的是俄语,所以英文不好,而以当时官方语言以英文为主的香港来说,不懂英文真的太吃亏了。本来有机会到大学或中学去教书,但因为不懂粤语和英文,只能委屈自己去唯一普通话教学的小学当教师。
1949年后,各省来香港的人多了,从山东威海的警察到跑单帮的台湾客,在本地广东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为瞩目。当然,香港人所说的上海人,不一定真的是上海人。根据1950年上海的人口调查,上海居民只有15%是原居民,48%是江苏人,26%是浙江人,还有各省的人,包括广东人。广义的上海人让香港的文化氛围产生变化。他们私下可能操各种方言,但他们的文化产品是用国语的——国语顾名思义在民国时期已经是全国的普通话,而上海在1949年前是民国的、国族的、国语的文化生产的独大中心。
一时间国语文化在香港所占的份额大增,而在香港制造的国语电影及国语“时代曲”甚至在势头上盖过本地的粤语电影、粤语流行曲,虽然在人口数量上操粤语者占绝大多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台湾的国语书和国语电影在香港亦甚受欢迎,甚至来自台湾的新国语歌也曾风行一时。大陆普通话电影由《刘三姐》到《大闹天宫》动画到样板戏,都曾安排在左派自己的院线上映。也就是说,1949年至七十年代初,香港曾有过二十多年的国语文化流行期。
许老师接着说:“当时香港还在殖民时期,内地来的人很容易受到排斥。那时还没有普通话这一说,而是称之为‘国语’,所以内地来的老师,就被划分为‘国语’教师,薪水很低,只能在私立学校教。他们的工资与公立学校的香港教师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正比。
“六十年代初,教学上用的课本一直是乔研农的说话课本,我1957年在内地首度学汉语拼音,到香港又学习注音符号,与现在的汉语拼音不同,这一套教学方法持续到七十年代初。那时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当院长的老同学介绍一位来香港开会的语言学家到我家里住,他说你们普通话教学,没有理由不用汉语拼音吧?要想融入国际社会,一定要学会这一套汉语拼音。他还批评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自己都不率先提倡,真是不应该。你要不愿意跟校长说,我去说!后来校长听取了语言学家的建议,把编写汉语拼音教程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前后用了几年的时间,编出了一套学校专用的汉语拼音教材,有了这个基础,后来又帮几家出版社编了几套汉语拼音教材。那时候啊,白天要上课,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编写,常常弄得自己睡不好觉,老是牵挂着这事。每天四点钟必须起床开始工作,多年后的今天,我的生理时钟依然很忠实地跟着当年的习惯,一到四点就醒。从前一看到‘四’字就会有一种怕怕的感觉,持续几年时间要在那个点起床进行编写工作,每天好像都要在挣扎中‘死’一次。哈哈,这么多年过去,都不知‘死’了多少回啦!真不知自己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许老师的描述轻描淡写还不时带着幽默调侃,可想到她当年编写汉语拼音教材时的艰辛时,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为了普通话教学在港取得更好的成就,如此艰辛地付出却如此低调地带过,我怎能不被眼前这位前辈感动?怎能不对她肃然起敬?
许老师继续说道,前几天,几个朋友在喝茶时讨论,有人说:“只要勤呀,你就会富;但你懒呀,就一定会穷。”我就忍不住和他们辩论,我说勤也未必富,懒也未必穷,教书匠都是默默耕耘。这个社会很难分配公平的,你看人家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地,根本不如那些股票经纪或者明星,一次交易或一次登台可能赚你一年两年的薪水。正如我们这些教普通话的人,都是默默耕耘、默默奉献的。那个年代的我们,就算付出百倍的时间和心血,依然很穷,依然过着清苦的日子。
“不过我仍然庆幸自己能够在同一间小学呆了那么多年,现在我的很多学生都成就斐然,不时会请我吃饭聚会,在育人育才这一点,我相信自己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1994年,在这间名校教了三十个年头后,因与当时的校长,也是我的好朋友教学理念不同有了分歧,我离开学校到城市大学开始正式教普通话。大学毕业时,曾有分配到广西师院教语言的机会,但因为我觉得教中文更有内涵而选择了到另外一所中学教中文。到了香港,语言成了谋生的技能,也只好放弃理想,投入到普通话教学的队伍中去了。有人说,时势造英雄,那个年代,想要出头很容易,但我没有什么野心,一辈子就安安静静教自己的书就好了,成不了什么英雄。
“城大的教学工作对搞了半辈子语言教学的我来说很轻松,对象是大学生或公开进修课程的成人,学生们都很喜欢我,在那里上课感觉非常愉快。每周有十几节课,一节课四百元,一个月也有两万多元,我感到非常满足,这比干了三十年的那间名校一万多的工资还要高。我这人真是不求上进,不喜欢往前冲,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很容易满足,所以我这一生人都觉得很轻松。
“有一次中文大学校外课程的负责人问我,愿不愿意夜晚到荃湾深井去教嘉顿集团的职员?我却忽然来兴趣了,跟儿子说起这事,儿子也兴致勃勃地说可以呀!我下班回来送您过去,到荃湾吃饭,然后再去接您。一旁的婆婆听到我们母子俩的对话,笑着问我们:你们俩这汽油不要钱呐?还要到荃湾吃顿饭,可能上课的钱还不够付吃饭的钱吧?会不会算账的?当时我就哈哈笑着说:这样好玩呀!既可以增加母子相处的时间,又能帮到别人学习普通话,其实是赚了呢!婆婆也只能笑着摇摇头说:看来你们这是享受大过利益啊!”
说到香港校际朗诵节的推广和评委工作,许老师满怀感慨地说:“从一到那间名校教书几乎就开始了。当时带学生去参加比赛,那时还没有太多人会说普通话,所以知道的人和参加的人都不算多。那时候常常拿奖,记得有一次评委给了我的学生双冠军,一个场次里面产生双冠军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两个都是我的学生。那时候我们学校在校际朗诵节是‘八面威风’啊!拿了全场总冠军。因为我本身是学中文的,在南京上小学时就常有赵丹、王丹凤、秦怡、张瑞芳等大艺术家到校讲课、辅导朗诵,一直都很喜欢这门艺术。所以我教学生便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心得,把每一位作者的作品都演绎得生动活泼。后来,经过推荐就加入了朗诵学会评委会,一做就做了几十年。有一位我很敬重的老评委临退休前郑重地对我说:许小姐,有一件事我想要拜托你。就是在比赛时候,学生读完作品名字后一定要说‘作者’二字,再说出作者的名字,不然对作者不尊敬。假如作品名字叫《乌龟》,你说完‘乌龟’就直接说作者名,那作者还不成了乌龟了,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也郑重地点了点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每一届的比赛我都会强调这个事情,为一个老评判的委托,也为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缺乏的一种仪式感,我做足了五十几年。今年退休前,我再次申明,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有些该坚守的事情还是要坚守,我卸下这个重任,把它交给你们了!”
“在评委会我还认识了阿浓,成为很好的朋友,阿浓介绍我加入儿童文学会,后来明华出版社请我写儿童故事,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许老师亦是香港的儿童文学名家,任某文化组织会长六年了,退休后仍热衷为下一代做播种、培育工作;她写了很多反映真善美的儿童故事和教育散文。
“在儿童文学会组织的活动中,常被邀请给孩子们讲儿童诗的朗诵,在活动中又认识了搞儿童教育的陈淑安,她写的儿童诗也很有趣,为人也好,我就请她到校际朗诵协会来,在比赛中加设了幼儿组项目,由陈淑安负责,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一直互相支持互相勉励。前两年她在美国一家老人院去世了,我又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不仅文章写得好,还会弹琴唱歌,很多朋友为了缅怀她,为她出了一本纪念专集,每人写一篇纪念文章,也算是对她一生的肯定。所以说时间很快的,一生一晃眼就过去了。这一刻,很多故人涌出来,很多故事涌出来,经历的时候只是经历,经历过后就成为别人口中的故事,而很多的故事串起来,就是人生。
“人就好像大海里面一个小小的波浪,很快就被后面涌来的浪淹没了。你现在知道还有个陈淑安,再过几年,又有谁知道这个人,记得这个人?你去中文大学看看,学校里挂着很大一条横幅:谁是鲁迅?若干年后,我们的后辈,还有几个人会认识鲁迅?这个我们都不敢说。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做什么事都轻轻松松去做,什么功名利禄,没有多大意思。好好地过每一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一生轻轻松松就过去了。你做了什么,付出过什么,得到过什么,失去过什么,没有人会记得,没有人会提起,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太计较,很快都会烟消云散了。
“今年很巧,五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叶玉树见面时送了他写的书法给我,就一个‘静’字,而阿浓也从国外给我寄来他写的一个‘怡’字。这真是告诉我从此要静下来了,怡然自得地享受人生。其实我非常满意我的人生,不谋取,不钻营,不算计,不执迷。轻轻松松就过了一辈子,就算苦也会学着苦中作乐,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我觉得人的一生变化实在太大了,起起落落,变幻不定,你要没有一个好的心态,从一个好的角度去理解人生,你是很难挺过去的。
“若说我的人生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没有去学一门艺术的技能,比如画画、书法或者是一种乐器。语言这东西太过飘忽,没有植根在一个深刻的基础上,就好像漂在水面的浮萍,没有根,没有实际的东西。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一定会学习哪怕小小的一样东西,一个小小的技能,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深度。扎扎实实地去做,你的根扎得越深,你才能在这世界留下点什么,而不是这样浮光掠影地一闪而逝。”
与许维琳老师短短的一次茶聚,散散淡淡的谈话中,信息量实在太大,收获的东西实在太多。从1962到2019,许老师经历和见证了太多的东西,那诸多的感慨无法用语言描述,我把它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去感悟,让更多的人去得益。我在安静聆听的同时,亦在反省自己的人生。我,做到无悔今生了吗?
……
节选自《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10期